男女主角分别是胡为民龚秀珠的女频言情小说《重生79:离婚后,我成了大文豪全文+番茄》,由网络作家“梁园筑梦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龚秀珠出身在教育世家,爷爷是燕京大学的教授,父亲虽然没有教书,却也是燕大的教职工。她的母亲黄连英也不一般,父祖辈是商人,只不过后来被打成了资本家,算是家道中落。她自小便受到家人的宠爱,直到那上山下乡的苦差事落到她头上。一道政策下来,她便从燕京城里的大小姐,变成农村知青。农村的苦日子,让她现在还做着噩梦。在那个讲究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,女性的身份让她得不到半点优待。还好,她知青的身份以及美丽的容貌吸引了许多农村未婚男青年。那时候,胡为民也是她的追求者之一。七十年代,知青生活非常苦,更何况龚秀珠孤零零一个人。在遭受生活的毒打后,她觉悟了。原本,她是看不上那些泥腿子的,奈何,她急需一个人替她挣工分。一番挑选后,胡为民勉强进入她的视野。后来...
《重生79:离婚后,我成了大文豪全文+番茄》精彩片段
龚秀珠出身在教育世家,爷爷是燕京大学的教授,父亲虽然没有教书,却也是燕大的教职工。她的母亲黄连英也不一般,父祖辈是商人,只不过后来被打成了资本家,算是家道中落。
她自小便受到家人的宠爱,直到那上山下乡的苦差事落到她头上。
一道政策下来,她便从燕京城里的大小姐,变成农村知青。农村的苦日子,让她现在还做着噩梦。
在那个讲究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,女性的身份让她得不到半点优待。
还好,她知青的身份以及美丽的容貌吸引了许多农村未婚男青年。那时候,胡为民也是她的追求者之一。
七十年代,知青生活非常苦,更何况龚秀珠孤零零一个人。在遭受生活的毒打后,她觉悟了。
原本,她是看不上那些泥腿子的,奈何,她急需一个人替她挣工分。
一番挑选后,胡为民勉强进入她的视野。
后来一起工作的过程中,龚秀珠对胡为民了解越发深,加上他有几分这个时代农村青年少有的特质,让她心中的天平砝码,对他偏移了几分。
一次去河边洗衣服时,胡为民又救了知足落水的龚秀珠。半推半就,两人结成夫妻。
本来,龚秀珠以为自己要当一辈子农村媳妇,没想到命运眷顾,她有了回燕京城的机会。
面对机会,她毫不犹豫选择回家,哪怕要带上胡为民这个‘黑点’。
回到燕京,和家人团聚,龚秀珠从未在外人面前承认胡为民是她的丈夫,而是和家里人商量一番,谎称胡为民是她的表亲。
就这么过了几个月后,她是彻底不想再和胡为民有所牵扯。
想到这里,龚秀珠的情绪越发激动起来:
“离婚,爸妈,我必须尽快和胡为民离婚!我以后还要考大学,怎么能有个当农民的丈夫呢?”
黄连英很认同大女儿的看法,她不住点头,附和道:“秀珠说得对,咱们家可是书香门第,而那胡为民一个泥腿子,如何配做咱们家的女婿!”
龚修文皱眉,横了妻子一眼,有些不满,“这话在家里说说也就罢了,不能对外人面前提起。”
他也认同妻子的说法,但有些东西只能心照不宣,能做不能说。
时局才刚刚好起来,他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。
“我又不傻。”黄连英小声嘟囔着,接着又看向另外两个儿女,“小成,秀秀,你们怎么看?”
胡为民的大舅哥龚成挠挠头,面露为难之色,“爸妈,咱们这样做不好吧?秀珠下乡的时候多亏了为民照顾,现在日子好起来了,咱们家就要和他撇清关系,岂不是翻脸不认人?”
“哼!”龚修文对儿子那迂腐劲大为不满,什么叫翻脸不认人?
他们是书香门第,结亲也要门当户对,以前便也罢了,现在他们家好起来了,泥腿子出身的胡为民哪里配得上他的女儿。
龚成见父亲面色不善,身子徒然一抖。在这个家龚修文是那个说一不二的存在,哪里容得下小辈反驳。
黄连英双目喷火,指着大儿子的鼻子呵斥道:“小成,你怎么能向着外人呢?要不是秀珠,现在复读考大学的就是你了!”
“妈,我......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龚成闻言,连忙摆手,最后只能苦着脸道:“唉,这事你们做主就是了。”
黄连英见儿子低头,严肃的面容缓和了几分,接着她又看向一脸纠结的小女儿,“秀秀,你还小,妈就当你同意了。”
龚秀秀咬着嘴唇,鼓起勇气,看向父母:“爸妈,离婚不是小事,事关姐姐的幸福,是不是......”
她倒不是觉得姐姐不应该离婚,只是觉得下的这个决定有些草率。
龚秀秀和胡为民接触时间不长,知道这个便宜姐夫虽然没本事,但胜在憨厚老实,很听姐姐的话。
贸然离婚,难道就能保证姐姐下一任老公能对她更好?
黄连英摆摆手,完全没把小女儿的话放在心上:“你还小,这是大人的事,你就不要管了。现阶段,争取明年高考考上好大学才是要紧的事。”
龚秀珠见家里人都支持自己,眼中带着希冀,看向自己的父亲。
在这个家里,龚修文才是那个真正拿主意,做主的人。
他看到家人的目光集中到他身上,沉吟片刻,才缓缓开口,“秀珠和胡为民离婚的事情就这么定了,晚上等他回来,我再和他详谈,争取让他和秀珠好聚好散,以后别再骚扰咱们家秀珠。”
“谢谢爸,不过......我怕胡为民不答应。”得到想要的答案后,龚秀珠心中大定,旋即想到胡为民的执着,秀眉微皱。
“呵,胡为民的工作都是我给他安排的,他要是识时务也就罢了,要是不识好歹......”龚修文没有说下去,话里话外,意思已经很明显。
有了父亲的保证,这下龚秀珠彻底安心。
......
在龚家人商量着如何让胡为民答应和龚秀珠离婚时,他已经在燕大门卫岗上班。
此时的他正在阅读着从燕大图书馆借来的文学名著。
既然想靠着文学创作改变命运,那丰富的阅读量是必不可少的。
虽然他脑海中有来自后世的古今名著,可他一个高中文凭的农村青年,突然在杂志上发表作品,还是有些匪夷所思。而他现在所做的,就是在凹人设,让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,变得有迹可循。
说不定若干年后,他一边当门卫一边搞创作,还能成为一件美谈呢。
此时,门卫室内,铁皮收音机在窗台上滋啦响着新闻:“中东某国爆发人质危机......美利坚总统决定......”
正听着新闻,邮递员叮铃铃骑到燕大门卫处旁:“胡为民!有你的邮件!”是远在沪上文艺出版社发来的,这家出版社,正是《故事会》的主办单位。
《故事会》创刊于1963年7月为双月刊,1974年3月《故事会》改刊名为《革命故事会》,1979年1月《革命故事会》恢复原刊名《故事会》。
这个时期,文坛的主流思想,始终被《人民文学》《萌芽》《收获》等大型期刊把持,它们追求严肃文学,讲究思想深刻,文学性强,反映时代云云。
但同样的,通俗文学也有不小的市场,《故事会》正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胡为民之前投稿的文章被文学期刊拒稿,因此,他想到了更通俗点《故事会》,没想到这么快有了结果。
他攥着邮件,心脏嘭嘭直跳。
就在胡为民为创作自己第二部短篇作品努力之时,沪上印刷厂为了《故事会》79年第六期顺利发售,已经忙碌了数个通宵。
印刷厂的工人还能三班倒休息休息,印刷机就没停下来过。
在各个部门的辛勤努力下,一本本崭新印刷出来,还带着油墨香气的杂志被打成捆装车,发往各个报刊点和邮政局。
此时《故事会》复刊尚且不足一年,发行渠道比较单一,发行范围也有限。除了北上广等各家杂志社必争之地外,只有江、浙、皖等少数几个省份。
沪上闸口某弄堂口。
褪色的灰墙上刷着“团结一致搞四化”标语,墙角青苔斑驳。
木板搭成的流动报刊点挂着麻绳,夹着《新民晚报》《大众电影》,边缘散落着《少女之心》《一双绣花鞋》等地摊刊物。
卖报人上声穿着藏蓝色上衣,吆喝声混着隔壁老虎灶飘散出的水汽:“新到的杂志,两角一本!”
这处流动报刊点旁,不时有行人驻足,询问着“有没有攒劲的小说”等令人难懂的话。
小贩也不会让顾客失望,做贼似的从怀里掏出一本黄皮封面小说递给顾客,顾客翻看两眼后,则露出如获至宝的笑容。
给钱,拿书走人,干脆利落。
改开后,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的需求空前高涨,工人阶级有钱,还有一定文化,是文学杂志的主要受众。
纺织厂青年工人李卫国就是个文学青年,他21岁,没有结婚,除了攒钱娶媳妇的老婆本外,他的大部分收入都用来购买文学杂志。
他捏着自己省吃俭用,攒下来的一块钱,想买本《收获》或《十月》他认为这些杂志“有思想深度”,工友们也都喜欢这类杂志。
“同志,要什么杂志?新到货的《少女之心》看吗,比以前的手抄本咂劲得多。”
“有《收获》吗?”
“没有。”
“那《十月》呢?”
“也没有。”
“怎么啥都没有?”
“我这就小摊位,卖的都是《少女之心》这类小说。你要想买《收获》《十月》,你去新华书店呗。”
“唉。”
李卫国叹口气,摊贩说得那些他看过,有一次在厂里看,还被班长批评,自那次以后,他再也不敢看那种小说。
摊贩见他犹犹豫豫,指着角落里的一本杂志,问道:“有《故事会》要吗?也是正规杂志。”
“有《故事会》?也行。”
李卫国顺着摊贩的手指,瞥见角落里那本《故事会》,封皮是手绘的工农兵群像,标价一角五分。
《故事会》是沪上本地杂志,在本地工人群体中间颇受欢迎,只是目前该杂志刊登的作品都是些特殊年代的手抄本,或者没什么特点的小故事,格调不够高。
“算了,总比空手回宿舍强,明天有时间,再去书店买《收获》吧。”
李卫国点出一毛五分,从摊贩手中接过《故事会》。指腹蹭过粗糙的再生纸,瞥见内页标题《会说话的骷髅》,嗤笑:“地摊文学就爱搞封建迷信。”
他随手翻到《会说话的骷髅》那页,准备好好批判一番。
开始之时,他的表情还带着几分不屑一顾,可随着阅读的深入,他的神情越发凝重,已然沉浸在故事中。
两天后,何成伟坐着绿皮火车,一路晃到燕京。
他是土生土长的上虞人,从小到大没有跨过长江以北,这回沾了胡为民的光,出差来到祖国伟大首都燕京,心情也是激动不已。
要不是有任务在身,他肯定会饱览伟大首都的如画风景。
紧了紧身上的包,何成伟顾不得身上的疲惫,问清目的地方位后,坐着汽车向着燕大一路进发。
一路下来,他发现自己有些低估北方天气寒冷。
冬天到来,天地一片萧瑟,他的身体也被北风吹得瑟瑟发抖,好在想到就要见到胡老师,他的心里一片火热。
从汽车上下来,何成伟在热心市民的指点下,找到了燕京大学的校门。
当他看到燕大校园大门时,他心里别提有多羡慕。
这可是燕大啊,整个华夏最顶尖的学府之一,出过多少名人高官。对他这样的文人来说,说是圣地也不为过。
裹了下稍显单薄的上衣,搓了搓手,何成伟走向门卫室。
他发现门卫室里坐着位老同志,敲响了门卫室的门。
“您好老同志,我是沪上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的编辑何成伟,我是来找贵校的胡老师。”何成伟自我介绍一番后,又取出介绍信,“这是我的介绍信。”
“哦,是何编辑啊,您在本子上登记一下就可以进去了。”
高师傅看过介绍信,发现没问题,便笑着将何成伟迎了进去。
“谢谢老师傅。”
此时学校已经放学,胡为民也下班吃饭去了。
“同学打扰一下,我是杂志社编辑,请问胡为民胡老师的办公室在哪?”
“不认识?好吧。”
“同学......”
何成伟打听一圈,没打听到叫胡为民的老师或者同学。
别说学生不知道,就连老师也不认识胡为民这么个人。
“奇怪,胡老师给我的地址就是燕大啊?”
眼瞅着天快黑下来,何成伟心中越发焦躁。
他也想过去学校教务处问问,不过学校老师都下班了,他也只能明天再来。
出师不利,何成伟心情低落。
当他路过门卫室的时候,高师傅奇怪地问:“何编辑,这么快就出来了?”
“唉,别提了。我问过很多老师同学,他们都说不认识胡老师。可明明胡老师就是你们燕大的老师,可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认识呢?”何成伟忍不住将心中的疑惑说出来。
高师傅热心道:“何编辑,我们学校的老师我差不多都认识,你说的胡老师全名叫什么,说不定我能帮你指指路。”
“那感情好,胡老师全名叫胡为民。”何成伟抱着试一试的态度,告诉了高师傅。
高师傅愣住了,旋即掏了掏耳朵,不可置信道:“谁?你说是谁?”
“胡为民,胡老师。”
再三确认后,高师傅神情古怪地问:“胡为民......小胡?何编辑,你是不是找错人了?”
“没有,我很确定。”何成伟确信自己不可能找错人,旋即问道:“怎么,高师傅,您认识胡老师?”
高师傅挠挠头,为难道:“我倒是认识一个胡为民,但他可不是我们燕大的老师。”
“难道他是学生?”
高师傅摇头。
“是教师家属?”
高师傅继续摇头。
何成伟苦笑道:“老师傅,您可把我搞糊涂了。”
思虑半晌,高师傅才开口道:“我认识的胡为民他和我一样,是燕大的门卫。”
“什么?”何成伟瞪大眼睛,嘴巴张得老大。
他对胡为民的身份有过许多猜测,唯独没想到那位神秘作家只是个燕大门卫。
“不可能,能写出那种文章的,不像个新人,更何况......”
何成伟的头摇晃得如同拨浪鼓一般,嘴巴里不停嘀咕着高师傅听不懂的话。
高师傅附和道:“是吧,小胡虽然爱学习,但你说他写什么文章发表感觉太荒谬。”
他虽然挺喜欢胡为民,却也不太能接受自己的门卫同事突然变成大作家。
毕竟是作家,搁皇帝在位的时候,那不是文曲星嘛。
不可能!
就在两人觉得荒谬时,吃饱喝足的胡为民跟老大爷一样,迈着八字步,晃晃悠悠走回来了。
“呦,高师傅,您有访客啊?那我在出去转转。”
胡为民见着何成伟,笑着和高师傅打了个招呼,便准备离开。
“等等!”
正当胡为民准备离开时,何成伟叫住了他,“您是胡为民......胡老师?”
“胡老师?这个称呼新鲜。”胡为民也不准备走了,他关上门,笑呵呵道:“这位同志,我是胡为民,但不是什么胡老师,只是燕大的一个小小门卫。”
何成伟想了想,进一步询问道:“胡......胡为民同志,《故事会》上面那篇《会说话的骷髅》是你写的吗?”
“你怎么知道?”胡为民眯起眼,旋即想到什么,猜测道:“难道您是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的同志?”
这下何成伟确信无疑,眼前这位穿着朴素的帅气青年,正是他要找的胡为民胡老师。
他激动万分,窜出一步,抓住胡为民的手,几乎热泪盈眶,“胡老师,我总算找到您了!”
胡为民有些莫名其妙,寻思着自己就是个小作家,也许在有些人眼里,连作家都算不上。眼前这人既然是《故事会》的编辑,至于见到他这么激动吗?
“胡老师,我是《故事会》的编辑叫何成伟,是您的责编。”何成伟自我介绍一番后,又补充道:“您的那篇短篇是我负责推荐的。”
胡为民听到何成伟的名字,也是眼前一亮,他感激道:“原来您就是何编辑,我要谢谢您,您采纳我的那篇文章,可是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啊!”
高师傅见两人热络的样子,整个人都惊呆了。
他没想到,自己的这个对班小胡,哦不,是胡老师,竟然真的是作家。
这么一瞬间,他有些惶恐不安,寻思着自己平日里有没有得罪过胡老师。作家哦,可不是他这个小老百姓能得罪的。
胡为民不知道高师傅心里想了那么多,此时他只感觉缘分之奇妙,竟然在燕京城见到了自己的责编。
他的感激不是作秀,从某些方面而言,何成伟真是他的恩人。
胡为民以后要是出名了,说何成伟是挖掘他的人一点问题没有。
激动过后,胡为民问道:“何编辑,您这次是来燕京公干的?”
他没自大到认为何成伟是专程来找他的,那可是《故事会》,在通俗杂志领域无可争议地存在,巅峰期单期卖到过760万册。
即使是现在,他觉得《故事会》卖个百来万册也没问题。
自己一个新人,哪里有那么大的脸。
胡为民这就是理解偏差,他习惯性地将未来巅峰期的《故事会》等同于现在。
他要是知道现今《故事会》上刊发的作品,以及单期最高销量,就不会感觉奇怪了。
不过,这个误会无伤大雅就是了。
“哈哈,胡老师,我是奉命来找您的。”何成伟笑了笑,看了眼门卫室逼仄的环境,皱眉道:“胡老师,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,我能不能去您家拜访,到时候咱们再详谈。”
“啊?”
“怎么,胡老师不方便吗?”
“倒不是有什么不方便。”胡为民挠挠头,指着四周尴尬一笑,“这里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。”
何成伟愕然道:“什么,您这样的作家怎么......怎么住在这里?”
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为他们杂志社提升十几万销量的作家,竟然连个正经的住处都没有。
“这......我是从乡下来燕京投奔亲戚的,有个住处和工作已经很满足了。”
胡为民想了想,敷衍道。
真实原因他不想说,算是为自己和龚家各自保留一分颜面吧。
何成伟无力吐槽,到底是什么奇葩亲戚,把胡老师这样的天才作家往外推啊!
就在他还想说什么时,高师傅突然道:“哎呦,饭吃太饱,肚子胀得慌,你们继续聊,我出去遛弯消消食。”
说完,他笑着离开了门卫室。
就刚才那一会儿,他已经吃够了瓜,再不走,就是没眼力劲了,不合适。
高师傅走后,两人都放开了一些。
“何编辑,不好意思,刚才光顾着说话了,我给你倒杯水吧。”
“谢谢。”
何成伟也不客气,他刚进门时身体都还在发抖,现在都没缓过劲,喝点热水暖暖身子也好。
喝了一口热水,他总算觉得舒坦了些。
两人坐在床边上,胡为民才疑惑地问道:“何编辑,您还没说呢,您一个杂志社编辑,特地来找我是为了什么?”
“胡老师,您上一部短篇作品刊发后,在读者中间的产生了极大影响,口碑也非常好。不瞒你说,我这次来呢,是来找您约稿的。”何成伟诚恳地说道。
听到约稿,胡为民来劲了。他现在正缺钱呢,何成伟算是瞌睡送枕头来了。
“那感情好,就是这约稿有什么说道没有?”
“只要作品质量上佳,不拘是短篇还是中长篇,我们杂志社都收。”
“稿费怎么说?”
“千字七块!”
比之前的千字稿费还提升了一块,胡为民狠狠地心动了。
1979年的冬天,燕京城格外的寒冷。
天还没亮透,胡卫民就被院角公鸡的啼声吵醒了。他轻轻掀开打着补丁的蓝布棉被,不忍心叫醒依旧在睡觉的妻子,简单套上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装,踩着绿面布鞋推开屋门。
院里飘着煤烟味,一位上了年纪的中年妇人正蹲在屋檐下的煤球炉子前,正用火钳子捅炉眼,铝锅里咕嘟着棒子面粥。
“妈。”
“小胡,去胡同口打豆浆!”妇人听到胡为民的声音,头也不抬地喊。
“还有,说了多少次,在院子里不要叫我妈,叫我婶。”
她语气冰冷,甚至带着一丝让人难以察觉的厌恶。
“哦......”
胡为民抿了抿嘴唇,神情有些落寞,最终还是点头应是。
中年妇女其实是他的丈母娘黄连英,自从他从遥远的乡村搬进这个家里,丈母娘就没给过他好脸色。
还有这个称呼,更是让他心里不舒服的同时,有着某种不好的猜测。
妇人冷漠的催促道:“知道还不快去,愣着干什么!”
胡为民回屋,拎起暖壶往外跑,胡同的青砖墙缝里凝着霜,更有远处飘来一阵炸油条的香。
副食店门口排队的街坊们裹着棉袄跺脚,王婶儿看到他后,夸赞道:“小胡,这么早就出来买早餐,真是勤快!”
“我年轻,起得早,出来买早餐也是应该的。”他咧嘴一笑,露出白净的牙齿。
七八十年代,国人的刷牙习惯并不普遍,甚至刷牙被视为一种奢侈的行为。此时,刷牙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规习惯,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如何正确刷牙,再有,一支牙膏动辄一两毛钱,对普通百姓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。
刷牙在七八十年代被视为一种“干部和读书人的派势”,普通老百姓很少有这样的讲究。因此,胡为民这口白净的牙齿,很是与众不同。
二十岁的年纪,一米八的大个子,英俊的面庞,加上一口洁白的牙齿,这让他还在村里的时候,不知道是多少大媳妇小姑娘暗恋的对象。
要不是他外在条件如此出色,凭他家堪称穷困的经济状况,也不可能战胜一众情敌,迎娶燕京来的女知青龚秀珠,最终抱得美人归。
一开始,他们小两口结婚后不说有多美满,却也称得上和和美美。
就当他以为幸福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,国家政策突然变化,允许知青返乡。
胡为民沾了媳妇儿和老丈人的光,得已离开乡下,来到伟大的首都,当个燕京人。
住进燕京的胡同后,他的家庭地位大降。
老丈人龚修文对他颇为冷淡,丈母娘黄连英对他时常冷言冷语,就连媳妇儿对他也是越来越瞧不上眼。
胡为民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,不就是政策变了,老丈人一家和媳妇越发嫌弃他这个农村来的土包子嘛。
他不是不知道,并且为此努力过,想要改变龚家人对自己的看法。
说起来,他也是有底气的。
他的灵魂来自二十一世纪,穿越前是个文艺工作者。
穿越后因为胎中之谜,直到最近才觉醒前世的记忆。完全觉醒前世的记忆前,他靠着脑海中的一些片段,写过一些小说,投递到各个杂志社。
他知道,就凭自己那高中学历以及老丈人替他找的门卫工作,在这个年代,只有写作才能改变他的未来,并且赢得妻子和她家人的尊重。
奈何,凭借记忆片段并不能写好小说,他的作品一直被退稿,他的行为反而迎来了龚家人的嘲笑。
但现在不同了,他完全觉醒了记忆,并且他发现自己对记忆中的作品印象非常深刻,就如同刻印在灵魂中一般。
这给了他十足的信心,坚信可以借此改变龚家人对他的看法。
而他也是这么做的。
前些日子,他重新写了篇稿子投递出去,相信要不了多久,杂志社采用他稿子的回信就会发过来。
“快了,苦日子就快过去了!”
打好豆浆,胡为民满怀信心地往回走。
“嘘嘘。”
胡同上空掠过鸽群,哨音像把碎银子撒进晨曦里。
回去的时候,他撞见前院返城的知青刘姐。她裹着红围巾,腋下夹着油印的《今天》诗刊,身上有股雪花膏的茉莉香。
《今天》创刊于1978年12月23日,由北岛、芒克等主办。它刊登小说、诗、评论和少量外国文学译介文字。小说虽然占据不小的分量,但影响力最大的还是诗歌。
在四九城的文学青年中,这份杂志的影响力非常大。
看了眼她手中的杂志,胡为民问:“刘姐,这么早就出门啊?”
“嗯,今天有诗社的活动。”刘姐笑了笑,解释了一句便匆忙离去。
看着刘姐的背影,胡为民眼中闪过一丝羡慕之色。
这年头,诗社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加入的,门槛很高。当然,对加入的人也有不小的好处。
“妈......婶子,我回来了。”
“怎么买个早餐也这么慢,真是干啥啥不行。”中年妇女嘟囔道。
胡为民尴尬一笑,心中多少有些无奈。
沉默半晌,他还是低着头,将装着豆浆的水壶拿进屋。
“爸,您早。”
“大哥早,秀秀早。”
胡为民进屋后,发现老丈人、大舅哥和小姨子都起来了,独独不见自己的媳妇儿。
“秀珠呢?”
“秀珠工作太累了,你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吧。”
老丈人面容严肃,语气平淡。
大舅哥龚成和小姨子龚秀秀对视一眼,没有说话。
龚家这两个年轻人对胡为民倒是没什么恶感,但同样看不起他,觉得他配不上龚秀珠。
因此,平日两人对他也是爱答不理的。
对此,从前的胡为民倒是习以为常,可现在的他心里很不舒服。
不是他敏感,就算后世的赘婿,地位都比他高,更何况他还不是赘婿咧。
没过多久,丈母娘招呼他们上桌吃早餐。
囫囵吃过些早餐,龚家人便催促他赶紧上班。
话也没有多生硬,只是说他一个新人,在单位工作要勤快点,宁愿早,不能迟。
当他出门没多久,龚秀珠出现在家人面前。
她一开口,便是石破惊天:“爸妈,我什么时候和胡为民离婚?”
《故事会》编辑部,主编办公室内。
负责发行的同志坐下后依旧情绪激动,满面通红。实在怪不得他激动,而是这个惊喜太大了。
他负责发行已经快两年了,去年不算,可今年,从没有哪一次发行带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。
往前数几个月,发行工作都是按部就班。杂志销量虽然有所增加,可都是几百上千增加,从来没有像这一期,杂志刊发不过两天,铺出去的杂志便卖光了。
从得到的信息中,他已经可以分析出,《故事会》这一期的销量怕是要上天了。
在主编的催促下,他平息一番激动情绪,开口道:“从今天早晨开始,我就接到各地邮局和书店的电话。他们都说咱们这期杂志销量非常好,上架没两天,存货就卖光了,顾客抱怨,他们也抱怨。他们给我打电话,除了抱怨外,还下了大批订单。”
“下了多少?”
“初步估算,有个四五万册呢!”
“四五万册?”
主编不由咋舌,这个成绩同往期相比,是翻了倍增长啊!
“不止这么多,现在统计的只有沪上的数据,江浙皖,还有燕京和羊城那边还没给我们打电话呢!”
“嘶!”
主编屁股坐在椅子上没多久,再次窜起来。
以小见大,沪上成绩都这么好,没有理由其他城市会差。
“快,你快回到岗位上等电话!”
主编已经可以预见,《故事会》第六期说不定会在今年年末放一个大卫星。
等负责发行的同志走后,他连忙打电话,安排印刷厂加紧印刷。
此时的他心潮澎湃,这一期杂志的爆炸性增长不仅是钱,更是自己的成绩啊!
果然,接下来几天,各地的订单陆续发过来,同沪上的订单加起来,超过二十万册!
销量暴增固然可喜,但主编更想知道的是原因。
一顿饱和顿顿饱之间,他知道该如何选择。
于是乎,主编安排编辑部的同志深入基层,打听这期杂志受欢迎的原因。
那位编辑同志也不负众望,深入基层后,很快打听到杂志爆卖的原因。
回来后,他不敢耽搁,当即找到主编汇报情况。
“主编,咱们这期杂志的一篇叫《会说话的骷髅》在工人读者中间的反响出乎意料的好。也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,吸引了其他普通群众的购买。”
“《会说话的骷髅》?”
主编皱眉,他对这篇短篇小说有些印象。当时只觉得这个故事新奇,却没有想到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。
“是的,读者们普遍觉得这篇小说层层反转,觉得很新颖,是他们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作品。”
“这篇作品的编辑是谁?”
“主编,是何成伟。”
“是小何啊,没想到他工作没多久,就给咱们编辑部带来这么好的惊喜。”
很快,主编叫来何成伟。
“主编,您找我?”
主编看着拘谨的何成伟,笑呵呵询问道:
“何成伟同志,你和胡成为同志相熟吗?”
“您说谁?”何成伟一脸茫然。
“胡为民啊,《会说话的骷髅》的作者。”
“您说他啊!”何成伟恍然大悟,旋即老实摇头:“不认识,他是通过邮寄投稿的作品,我觉得他的作品新颖,便决定采纳的。”
说完,他又小心翼翼地看向主编,惴惴不安道:“主编,是那篇作品有问题吗?”
“没有问题,小何啊,你可是给我们编辑部立了大功!”
主编接着将这期杂志大卖的来龙去脉说了出来。
何成伟闻言也是惊喜交加,同时,隐约觉得自己怕是发掘出了一位了不得的作家。
“小何同志,像胡为民同志这样,能为咱们杂志带来如此巨大销量提升的作家,一定要抓紧啊!”
“您说的是。”
“胡为民同志是哪里人你知道吗?”
“胡......胡老师的通信地址写的是燕大门卫室。”
“原来是燕大的老师或者学生,难怪有如此才华!”
主编瞬间觉得合理了,那毕竟是燕大啊。
胡适、茅盾、鲁迅可都是燕大的人,那里是有文学土壤的。
主编拍了拍何成伟的肩膀,笑呵呵道:“小何,我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,你敢不敢接受?”
何成伟站直身体,精神一振道:“请主编指示!”
“好,我需要你立刻买票出发,去燕京大学,联系到胡为民老师。”主编吩咐着,神情也变得肃穆起来,“咱们杂志这一期大卖固然可喜,但能不能稳定住销量,说实话,我心中也没有底。说到底,咱们杂志社之前靠刊发手抄本故事混个温饱可以,但真正想要发展,甚至追上《收获》《十月》《花城》这样的文学期刊,还是需要质量上乘的作品。
胡老师的作品有这样的潜质,我需要你去燕京找到胡老师,当面向他约稿。无论是短篇,还是中长篇,只要是好作品,咱们都收!”
说到最后,主编越发激动起来,“明年《故事会》第一期,我要让国内文学界看到咱们《故事会》的身影和力量!”
“小何,只要这个目的能达成,到时候你就是咱们编辑部乃至杂志社的大功臣!”
何成伟听的是心情激荡,主编的鸡汤让他面红耳赤,最后更是拍着胸脯道:“保证完成任务!”
......
《故事会》在发行城市销量暴增,其在燕京的销量较之沪上也不遑多让。
虽说严肃文学的盛世渐渐到来,但通俗文学同样有庞大的受众。
这不,龚秀秀所在的学校,渐渐流行起一份杂志,那就是《故事会》。
课间,高三年级一班传来嘈杂声。
“你看完没有,该我看了!”
“快了,快了,不要急嘛。”
“嘿,说好该我的,你抢我前面还不让我说。”
“你要是急,自己去买这期《故事会》不就行了?”
“就是反正也没多贵。”
男生们都在争相阅读《故事会》,搞得女生们都好奇起来。
女生们也想借来看看,只是听男生说里面有什么骷髅地,把她们吓到了,没敢看。
“秀秀,你说这什么《故事会》真有这么好看?”
龚秀秀身旁,一位梳着麻花辫的女生好奇道。
“不知道,我都没听过。”龚秀秀撩了下耳边的长发,不以为意道:“我们家订的都是《收获》《十月》,什么《故事会》从来没听过。”
麻花辫女孩羡慕地看向龚秀秀,她是知道这位同学家庭状况的,比她家有钱多了,什么文学杂志没看过。
“也是,《故事会》这个名字听着就不高级,估计也入不了你的眼。”
两人正说笑着,龚秀秀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。
“哎呦,这《会说话的骷髅》写得是真好,这个叫胡为民的作家也太有才了!”
龚秀秀突然看向那个说话的胖同学,”胖司令,你刚说作家名字叫什么?“
“胡为民啊,《会说话的骷髅》的作者。《故事会》为什么在咱们学校这么火,都是因为这位胡作家的故事写得新颖。”胖司令吹了一通后,晃着手中的杂志,笑着道:“怎么,龚秀秀同学也想看杂书?”
龚秀秀本想拒绝,可话到嘴边,却变了,“那你看完借我看看。”
“哎呦,龚秀秀秀秀同学想看,我怎么敢让你等呢。”胖司令笑着将杂志递给龚秀秀。
麻花辫同学惊讶道:“秀秀,你还真看啊?”
“就看一眼。”龚秀秀咬着嘴唇道。
究其原因,还是胡为民这个名字,让她做出如此离谱的决定。
“会是他吗?应该是同名吧,毕竟他一个乡村来的人,怎么看也不像是个能当作家的人。”龚秀秀心里嘀咕道。
龚秀秀接过杂志后,发现《故事会》的封面颇具特色,就是页数不多,也就一百页的样子,厚度和《收获》《十月》完全没法比。
翻开杂志,她很快找到和那个男人同名同姓作家写的文章。
故事是短篇,很快她就看完。
看完后,她发觉这篇作品颠覆了她对文学作品的认知。
一开始,她以为其中的内容是封建糟粕,结果阅读下来,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
小说里对人性丑恶面的揭露,简直让人叹为观止,为了揭露真相,更是层层反转,给了她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。
“这是一部可以在《收获》上发表的文学作品!”
龚秀秀感到惊艳的同时,又断言道:
“这样优秀的作品,绝对不是胡为民那样的农村青年可以创作出来的。”
这一天,龚秀秀下课回到家时,脑袋里还在回想着胡为民的那部作品。
饭后,她鼓足勇气问道:“爸,今后家里能多订一份《故事会》吗?”
“《故事会》?什么杂志?”龚修文摸不着头脑。
龚秀秀眼神闪烁道:“是一份来自沪上的杂志,我们学校很多同学都在看。”
龚修文放下报纸,问道:“杂志多少钱?”
“《故事会》是双月刊,每期只要一毛五。”龚秀秀连忙道。
龚修文点头道:“不贵啊,那行,家里今后就多订一份吧。”
“谢谢爸。”
得到父亲同意后,龚秀秀小脸红扑扑的,心中更有一种异样感。
她之所以会订购《故事会》,单纯是喜欢里面的故事,和胡为民这个名字没关系,对,真相就是如此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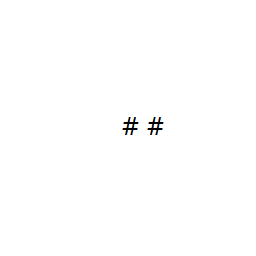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